甘孜日报 2017年08月16日

格绒追美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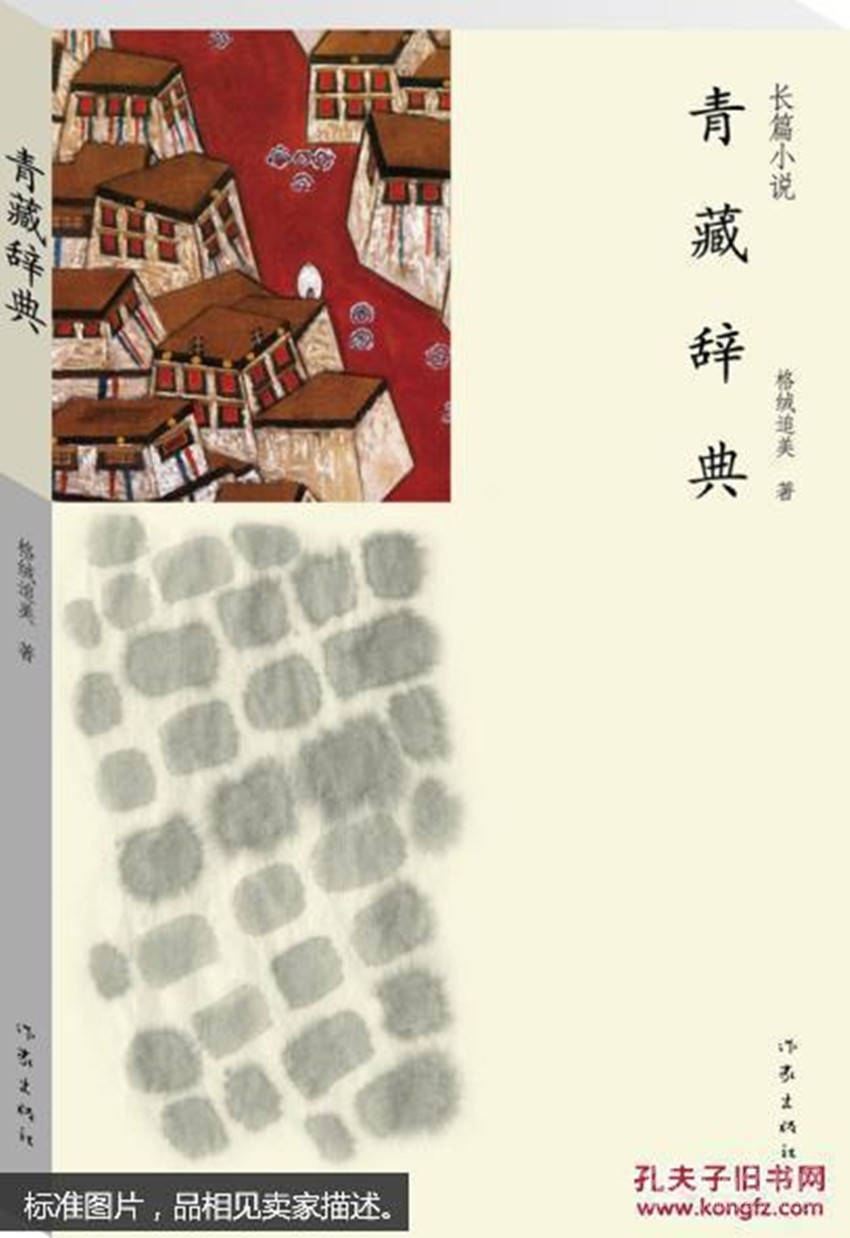
(三)
■范河川
格绒追美的文学作品是民族学者的觉醒,有着对信仰体系的审视和本真的解读。在传统文化中作为写作者和反思者,一定是在迷惑——觉醒——反思——抗争——觉悟的过程中,甚至是反复中。觉醒这是痛苦的角色,需要一生的付出和求索。笔者曾在《康巴传统文化的成因极其影响》中分析过“新旧行为规范交相混揉以及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无所适从的阶段。为什么传统伦理的转化进展一直远落后于社会其他变革之后?这是因为凡是涉及到与情感有关联的基本文化内容,如信仰、观念、态度等,在文化融合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不容易改变的。究其原因这是民族性和地域性赖以形成的核心,这个核心的部分如被改变,会整个打破原来的心理习惯和生活秩序,是一件极端痛苦的事。在身受文化冲突带来的痛苦中,只有极少数甘愿忍受并正视这种矛盾与痛苦,然后运用他清明的理智寻求调整之道,进入人格重建的过程。这是一个精神觉醒和革新的漫长过程,需要一生的奋斗仍未必能竟全功。因此多数人不能或不愿如此去做 ,有的仍固执于原有伦理体系,排斥新的伦理质素,以避免内心的彷徨和不安,有的则任其新旧伦理质素共存于人格内部,就不同情境随时使用互相矛盾的不同质素。前者的反应表现心理的逆退,后者的反应在过渡期中有助于心理的安全,但皆不足以促进文化和伦理价值的创新。”在格绒追美《青藏辞典》中有很多这样的精彩叙事。譬如:“自我是个无比顽固的堡垒,却也是解决在人类所有核心问题的中枢。因为自我是社会、环境、文化、教育、宗教等的缩影。一个人越是愚蠢他越是排外,从种族、国家、信仰、社会习惯等各个方面。自我如果囿于这些束缚,人类就会惹出一大堆问题,因此圣者说:认识自己是解决心理、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途径;人性皆相同,了解你的本性你就会了解世界的问题所在。”
“所有宗教都是通向‘神’的道路。人类创立宗教的目的在于,帮助生长在这些环境中的人知道并且理解:有一个时时刻刻存在的源泉,它在你需要时提供帮助;在你困难时提供力量;在你迷惑时提供清醒;在你痛苦时提供同情。或者说,它教导你最终发现了自己的神,你是你自己的神,你是你自己的造物主。所以宗教还是人本具觉知的探索,其中的仪式、传统、礼仪、习俗也具有巨大的价值,标志着某个族群或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作为黏合剂,还凝聚着民族的文化。”
“每个人心中都有神性的种子,每个人头顶都辉耀着神性的光芒,甚至每个人的双肩头顶都居有神灵。人啊,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个性化缩印,每个人都表达着神的自己。”
“神只存在与你不在场的时候。如果你在场,神会隐匿起来;你不在爱会献身。神就是你,你就是神——当然这个你不是前面的那个‘你’,而是‘无我’的你,全然摆脱一切二元论的全新的你。”
作为传统人能够选择宗教、神、自我如此拷问、解读,是对信仰体系本真的诠释。
信仰本身就是对神的体验和认识,其实宗教里的神和哲学中的神、小说中讲的神,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宗教中的神是化了化妆人格化了,
小说中的神更多是自我,通过艺术直观、宗教表象、哲学概念自己认识自己的精神。就是要构建一个它认为完美的信仰体系。
既不是相信宇宙中的一切是神所创造,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因果循环,靠内心的善恶道德法庭约束自己,相信“头顶三尺有神明”,
所以不敢胡作非为的信仰体系。也不是人的心灵被某种主张、或说教、或现象、或神秘力量所震撼从而在意识中自动建立起来的一套人生价值体系。从他作品中更多的是反思,主张与时俱进,天人合一与传统道德和进取心相融的信仰体系。体现信仰是灵魂的导航仪,反物质至上,主张精神不被物欲囚禁,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生命结局这种价值追求。“让我们超越和开悟”是追美写的一句诗,这是一名藏族作家对传统再认识的贡献。
格绒追美作品将艺术的触角伸向民族文化深层的反思,是他文学态度求志达道的纠结。
格绒追美在《涅槃再生》中写到“我将高扬信仰和自由的独立精神的旗帜。为雪域而歌,为人类广阔的心灵而舞。向着终极圣地坚定地走下去。”这既是他创作的境界,也是对民族精神与文化进行清醒而深刻的自我救赎,认识到了文学的意义不仅在其本身,而且在于由它信仰和自由独立的民族精神里。泰戈尔说一个人所追求的是希望看见在烧毁“旧事物”的火焰顶上出现光辉灿烂的“新事物”。
首先看他对文化管理的反思,“文化是政客们喜欢的最大的最深的框子之一。什么时候需要就当作旗子摇一摇,什么时候高兴了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装填。文化的真实地位是:文化是一点口红;如同秃顶者头上的三根毛发,也像妓女拂袖可抛。”其次是他对文学界所谓大师们的看法,“大师换美女无数。或许,这也是大师的标志之一?不然,大师能有什么吸引力呢?哈哈,大师,嫖娼狂与你同属一个类型吗?”文学是个很圣神的词,但他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是个形式,内涵是无所谓“文学”的,但是把文学装在文学里的人,越来越多。文学不是服装展览,也不是材料的堆积。而是作者通过提炼而成的生命体。至少也是一缕有生命体味的芬芳。”这种认识缘于政治人操弄文字“人类一旦进入操弄文字的时代,文字反而有人牵制了人类的思想脚步。文字的被神化,是人类的愚蠢行为之一。”如何摆脱这些束缚与制约,必须的挣脱缰绳,想办法突破。他认为“文学的宽广路子必然突破文字的局限,进入人类的大传统,这个传统包括史前文明,神话历史,文物图像,口传的活态文化,出图文字,文字之外天地人的所有信息等。文字的传统是个小传统,文字的叙述还有遮蔽和欺骗的作用。”
追美的作品处处充溢着深刻的反思,在传统文化的洗礼中润浸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作为一个民族的觉醒者,努力的拓展视觉,以抛砖引玉的态度展示思想。再看他充满矛盾、焦虑、纠结的创作路程。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在现实中磨砺着意志、理想,在藏族文学的苦旅中从怀疑、徘徊、醒悟中以求志达道的心态前行。每个路程许下心愿,如他所写“益西措嘉,莲花生大师的伟大密妃。杰哇将秋所著的《益西措嘉佛母密传》。介绍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总有一天,我会写出关于益西措嘉的一篇小说。”正是这样的精神境界,才有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开雾睹天的最真地文学信念。
格绒追美作品中藏民族信仰的精神家园与生命的叩问。在读格绒追美作品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他写的诗,他的诗清新优雅、纯净透明,含蓄委婉、富有哲理。他诗中所含巨大的力量,让人惊疑,诗歌实境完全有“情性所至,妙不自寻”的味道,诗是他心境的写照,也许是他身体原因,他在很多作品中不止一次的说到身体多病,写作中自然而然透露出当前状况,像是对着文学诗歌这个情人静静的叙述。叙述面对时间流逝的紧迫,对生命的渴望,对成就事业的心愿,对内心的真实一览无余的剖析、对白。当然,这其中更有寄托的精神家园——热爱故土,热爱甘孜。在《掀起康巴之帘》一书中的他在《康巴行吟》中写到:“在稻城亚丁,沐浴纯净、和善、安详的自然之光,心灵脱净了尘嚣、梦想、野心和俗事烦情,身心豁然亮丽。我们犹如初生的人子回到雪山、山峦、草甸、溪流、森林交汇构成的最初的洁净的自然怀抱,灵魂清纯,天地明朗、清爽——这莫非是世外桃源,一切都显示出清丽初绽的清晰迹象,混沌初开,和谐美洁。动情处,我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在遥远的稻城
太阳和月亮守护着圣洁的亚丁
童话和梦幻凝住皑皑的贡嘎雪峰
翠绿的森林 宽阔的草甸 清清的溪流
还有那莲花生的身影和祈愿
哦 圣洁的亚丁
哦 香巴拉之梦
引来多少朝圣者的脚步
去追寻这片神圣的净土和家园
在遥远的康巴稻城
莲花和星辰守护着圣洁的亚丁
希翼和梦想浸润贡嘎日松贡布
高俊的岩峰 迷人的冰川 翡翠的海子
还有那飞瀑鸟鸣和寺庙的法号
哦 圣洁的亚丁
哦 香巴拉之梦
让世人千万次深情向往
去追寻这片神圣的净土和家园”
涂鸿在《文化嬗变中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一书中讲:“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多是依山旁水而居的,连绵不绝的群山是少数民族的生命之源。从最原始的山神祭拜,到各种各样大山的奇异传说,山的意向从最初的崇高、伟大、秀美,到后来象征刚强、伟大、顽固、神秘、家园、黑暗、屏障等多重意蕴的延伸,都体现了世代与大自然相争相存的少数民族人民对于山的依赖与崇拜。共同的劳动生活、生存斗争使他们形成了对山的共同体认,而这种认识体现在创作中则表现为崇高、刚烈、奔放的艺术风格。”这在格绒追美《隐蔽的脸》中得到具体的印证。“我飞向了雪山正在升起的那个时代:空灵、寂静;飞向了人刚刚诞生彷徨之期:寂寞、孤单、而有充满了未知和好奇。啊,三千世界中的吐蕃之地被雪山环绕,像花白母牛的脊背呢;源自猴与岩魔女的藏人讲着阿巴支达魔语言。上部,满是草滩和森林,像一块平整的田地。”这段话我一直读成诗。藏民族的起源或者说心中的精神家园不正如此?因为信仰一个民族成为外界尊敬的群体,因为信仰生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的民族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我写作是有意义的,它应当汇入更多人类的声音中。让我像一只雪鸟从污浊的海上飞起,用清凉的鸣啼歌唱,翅膀舞动于雪山和草原的天空,描摹出五彩虹光。”《追美的诗其表达内容已完全超越了“言志”的范畴。诗中含蓄而敏捷地表现“自我”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在节奏中就产生了魅力无穷的力量。除了抒发情感表达理想之外,更有对世界认识的深入,对生活观察的全面化,对身边存在的世界的认知与呈现,一幅精神家园的意境画跃然而出。
把信仰的精神家园与生命的叩问放在这节讨论,这本身就超越的文学本身哲学的范畴。人们常常质疑一个民族的劣根性,也就是说表现与优秀传统文化不一致,出现叛逆,另类的时候的困惑。比如藏民族中有些人一边念叨着佛经,连虱子、老鼠、庄稼地里的虫害都阻止他人除害,可当为挣面子“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几杯酒下肚“青稞酒歌唱的时候世界就在手上”,打架、斗殴、用刀杀人,用枪报复等暴力行为与崇信的文化信仰相向而行,就会严厉的拷问每个藏族人信仰真的存在吗?
格绒追美作品不仅仅是对藏民族精神家园的赞美,还有对生命的叩问。纵观他的作品,他在勇于探索蕴藏于宇宙和自然中的生命意志与精神特质的同时,更隐形地传达了他的哲学观、自然观以及他对人生社会的深刻体察。看他《隐蔽的脸》这种印象会特别的强烈。通过我,晋美神子无形、虚无、偶尔幻化为具象,能自由穿越时空隧道,通过他的心灵、情感、思辨,直白,以暗示、烘托、对比和联想等方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创造出另一种意境。这其中有对信仰和血腥暴力复仇的生命叩问和人性反思。藏民族在虔诚信仰的同时,在狭小的艰难生存的空间中,械斗、复仇与佛教的教义背道而驰,在欲望、权力的角逐中纠结、矛盾,在与信仰不符的道德尴尬中挣扎甚至麻木。他在《青藏辞典》中反思“末法时代,污浊横行,一个自称有信仰民族中的三恶人,把刀尖伸向了人中之宝的一位仁波且。”《隐蔽的脸》中揭露庞措活佛被杀,旦巴头人设计谋杀大头人布根,白若斗村和东鈞发生的草场纠纷,还有复仇行为等等的民族劣根,让一个民族意识的迷茫与矛盾如铜镜一般照在阳光下,甚至是进行赤裸裸的讨伐。这缘于他不再为某种理论疲于应对,而是更多更自觉地去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民族。“一个民族作家,只要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自己民族的精神本质,那么他的作品就是跨民族、跨国界的,对于整个世界是有普遍意义的。”
追美的作品有通过“死亡”来震撼人的价值意识的主体意向和对生存本质的严肃哲学思考。《隐蔽的脸》我、晋美(神子)就是这样的符号。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rdegger)所说:“只有死亡才能排除任何偶然和暂时的抉择,只有自由地就死,才能赋予存在以至上目标”。因此选择死亡,并不意味着绝对虚无,它逼促着个体生命作出真正必要的创造,将有限的人生转化为“无时间的本质形式”的价值人生。
这就是藏人的境界,藏传佛教中祈求世界平安和对战争、疾病的焦虑。完全如同梅卓在该书封底所写之点睛:“从生到死,口述了藏人一生的酸甜苦辣;从人到魔,展现了传统碰撞的异样碎片;从有到无,包容藏族文化的哲学境界。格绒追美以华丽如诗的语言,带领我们探索藏传佛教的玄机,藏族文化的奥秘,藏族生活的现状,并逐渐深入到常住人性深处的那一片净土。”
最后用益西泽仁在《失去时间的村庄》作的序言结束。“格绒追美把文学的根深深扎在川藏高原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中,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特质,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说他的作品为藏民族当代文学创作增添了一笔十分艳丽的色彩。
格绒追美在这本集子的后记中说:‘地球的人类的村庄,故乡是我的村庄……我从村庄看雪域,看世界;看过岁月,看当下的进程,也窥视未来的面目。村庄也从里面看着外面的世界,冷冷地审视着我和我关于村庄的文字’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关于村庄的文字’写得更加美丽,因为他有这个潜力,也有这个能力”。